本文摘要:摘要:史蒂文斯皮爾伯格1998年執導的電影《拯救大兵瑞恩》毫無疑問成為戰爭電影的里程碑。與其他傳統的戰爭電影不同的是,斯皮爾伯格將反抗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作為發動戰爭的道德基石。大屠殺記憶作為一種象征符號被導演融入在電影敘事中,借此構建出更具
摘要:史蒂文·斯皮爾伯格1998年執導的電影《拯救大兵瑞恩》毫無疑問成為戰爭電影的里程碑。與其他傳統的戰爭電影不同的是,斯皮爾伯格將反抗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作為發動戰爭的道德基石。“大屠殺記憶”作為一種象征符號被導演融入在電影敘事中,借此構建出更具有普世意義的民族身份認同。對《拯救大兵瑞恩》中唯一的猶太人角色梅利及關鍵場景的文本分析和解讀,能夠發現影片對納粹大屠殺行動的“隱喻”和道德批判。導演將“大屠殺記憶”編織進電影情節中,通過描述戰爭的恐怖和犧牲引起觀眾對二戰期間猶太人悲慘命運的反思。電影和其他媒體還推動了大屠殺記憶的“美國化”進程,借此構造民族身份認同。
關鍵詞:拯救大兵瑞恩;大屠殺記憶;民族身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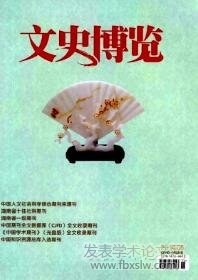
史蒂文·斯皮爾伯格1998年執導的電影《拯救大兵瑞恩》毫無疑問成為戰爭電影的里程碑。它不僅取得了商業票房的巨大成功,在有關“二戰”的文化記憶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紀念歷史并重塑民眾集體記憶,向戰爭中的犧牲者致敬。與其他傳統的戰爭電影不同的是,斯皮爾伯格將反抗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作為發動戰爭的道德基石。“大屠殺記憶”作為一種象征符號被導演融入電影敘事中,借此構建出更具有普世意義的民族身份認同。
一、作為視覺修辭的“大屠殺記憶”
作為電影中執行拯救瑞恩任務小分隊唯一的猶太人,列兵斯坦利·梅利(PrivateStanleyMellish)成為了觀眾和“大屠殺記憶”之間的媒介,他的表現以及和其他角色的互動推動了電影敘事的發展。梅利在電影中發揮了兩種作用,首先,他代表著世俗化猶太人,舉止行為表現出明顯的美國文化影子;其次,他的死亡激發了猶太“大屠殺記憶”中的關鍵因素——瀕臨滅亡的猶太人拼死抵抗,聽到呼救聲的美國基督徒同伴即影片中的翻譯厄本下士(CorporalUpham))卻無能為力,無人阻止納粹滅絕猶太人的恐怖行徑。下面選取影片中跟猶太士兵梅利相關的場景來解讀導演對“大屠殺記憶”的展現。
攻占了海灘后,士兵在搜索德軍戰壕時發現了一把希特勒青年軍小刀并把它交給了梅利。他拿起這把刀嘲笑著說:“現在它成為猶太安息日的面包刀了。”梅利說完,靠著戰壕忍不住開始哭泣。雖然美國猶太人在納粹大屠殺中幸免于難,然而猶太民族在“二戰”中遭遇的苦難給梅利心中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傷痛。此時的中士霍瓦特(SergeantHorvath)正在向寫著“法國”字樣的錫罐里裝土,旁邊是兩個標有“北非”和“意大利”的錫罐。鏡頭在霍瓦特、梅利和其他士兵之間切換,觀眾可以看到梅利哭泣時其他人眼神的躲閃。
這一鏡頭語言試圖暗示:無論漂泊多遠,無論在哪里戰斗,哪怕是到天涯海角,他們也不屈不撓地要終結這場可怕的戰爭。在猶太會堂和猶太家庭遵從的安息日傳統象征著人和上帝所訂立的盟約,而這把希特勒軍刀則致力于褻瀆和湮滅這種神圣性,作為猶太人的梅利不可避免地處在這種陰影之下。盡管信仰是神圣的,然而影片中的梅利已經是被同化的美國猶太人,觀眾從他身上看不到明顯的猶太痕跡。梅利在面對制造大屠殺慘劇的德國人時卻極力炫耀他的猶太身份:他在德國俘虜隊伍旁挑釁地搖晃著自己被“大衛之星”纏繞的胸牌,嘲笑著大喊“我是猶太人”。梅利試圖以這樣的行動來告慰死在納粹屠刀下的猶太同胞。然而無論他怎么做,逝者都不可能復生,梅利心中的傷痕也無法抹平。
梅利的死亡發生在電影最后一場激烈的戰斗中。下士厄本負責給位于二樓的梅利和另外一個士兵運送彈藥,然而他在槍林彈雨中被恐怖的景象嚇得呆若木雞,躲在柱子后面的角落里。樓上的美國士兵被擊斃,而梅利孤身一人在打完最后一顆子彈后開始和德國士兵肉搏,在此情境下猶太“大屠殺記憶”強烈浮現。梅利和德國士兵的打斗隨著鏡頭的搖擺使觀眾無比揪心,猶太人的處境岌岌可危。鏡頭不斷切換到瑟瑟發抖的厄本身上,他聽著樓上的打斗聲癱軟在地無法移動。此時的德國士兵已經將刺刀抵在梅利的胸前并將其緩慢刺入,同時喃喃自語:“這對你是一種解脫,很快就結束了”。在德國士兵刺死梅利后下樓時,近鏡頭掃過他衣領上的肩章,表明兇手是納粹黨衛軍成員,是把猶太人送進死亡集中營并執行“最終解決方案”的納粹精銳部隊。
從敘事角度來看,梅利死亡這一場景渲染了戰爭導致的悲劇性創傷,下士厄本這一角色在不同層面都發揮了作用。首先,作為觀眾的這一代人最初極有可能和厄本一樣選擇對戰爭袖手旁觀,而這樣的“不作為”產生的后果很嚴重。其次,厄本下士象征著美國士兵的情感創傷和犧牲。戰爭的殘酷給他們的身體和精神帶來了雙重創傷,電影男主角米勒上尉(CaptainMiller)也因為戰爭和死亡的壓力留下了雙手顫抖的后遺癥,這使得美國政府在戰后進一步關注士兵精神創傷問題。最后,守衛大橋的戰斗開始之前,厄本和梅利在門前的臺階上一起聽歌,談笑風生時建立了友情,寶貴的友情促使厄本對自己聽到梅利苦苦掙扎時的不作為充滿罪惡感,而觀眾通過這些具體場景的描繪更能體會到厄本的極度痛苦和悔恨之心。這些場景交織在一起表現出美國化的“大屠殺記憶”——因為對歐洲猶太人的遭遇沒有進行迅速而有效的拯救行動而充滿罪惡感。
二、“大屠殺記憶”的美國化進程
從19世紀40年代到60年代初期,猶太民族對大屠殺的記憶一直傾向于頌揚“華沙隔都起義”等英勇抵抗行為,選擇性地忽略了猶太人“像羔羊一樣走向屠場”的軟弱行為。1950年,以色列內政部和猶太復國主義宗教組織在錫安山上被認為是大衛王墳墓的地方為大屠殺受害者建立了一個悼念角,它被命名為“大屠殺地窖”。1951年以色列議會將尼散月第26天確定為大屠殺和隔都起義紀念日(theHolocaustandtheghettouprising),將大屠殺紀念日與反抗德國納粹的華沙起義聯系在一起;同一年,隔都起義紀念博物館建成。1953年以色列國會通過法律建立官方的猶太大屠殺紀念館。這部法案記錄了猶太人從納粹壓迫和死亡集中營時期就開始持之以恒的努力,紀念館將收集跟大屠殺相關的檔案資料、證詞、文件。
這些資料將向研究者和歷史學家開放,在他們重構歷史敘事時發揮作用。1959年又將原有紀念日改名為“大屠殺與英雄主義日”(theHolocaustandHeroismRemembranceDay),將對納粹的武力反抗看作是英雄行為,由此奠定了“大屠殺記憶”中的英雄主義基調,并通過《猶太大屠殺紀念法》對紀念日的儀式和日程進行規制[1]。以色列各地接連建立起紀念大屠殺的各種場所,包括猶太會堂、公墓以及公共廣場等。不同的紀念場所對大屠殺的原因以及對猶太人生活的深遠影響不斷進行反思。宗教與世俗、官方與民間紀念方式的差異也反映出各方考慮以色列未來政策時所秉持的不同政治理念。
猶太民族致力于利用已建立的大屠殺紀念館、國家悼念儀式以及教育體系等工具建構出經典的大屠殺敘事,確保猶太復國主義精神中的毀滅和重生、流散和救贖等主要因素得到認同。然而領導以色列建國事業的先驅們擔心“大屠殺記憶”在社會上的日益凸顯將導致以色列人對非猶太世界持否定態度,好像“全世界都在反對我們”[2]72,這些領導者們擔心大屠殺記憶和教訓在下一代中逐漸消逝。
在1956年大屠殺紀念日的講話中,阿巴·柯夫納(AbbaKovner)表達了這樣的困境:“有人說:不要忘記,最后他不會記得什么,因為記住一切使他癲狂;但要忘記一切是對生活的背叛。”[2]72他指出了兩條看上去自相矛盾的道路:一方面提出要限制大屠殺紀念活動,因為它可能使人在面對生活時灰心喪氣;另一方面他又把大屠殺紀念活動看作是打開新生活的鑰匙。忘卻并非是背叛大屠殺行為或者記憶,而是對生活本身的背叛。恰到好處地紀念和審視歷史是正確塑造猶太民族未來生活的鑰匙。
“大屠殺記憶”成為美國獨特的符號,表明流行文化和政治緊密相關。在“二戰”結束后的十幾年間,“大屠殺”并沒有從死亡集中營的回憶中直接被建構為具有象征意義的符號。集中營的幸存者在開始新生活后往往選擇對創傷記憶保持沉默,直到1959年“大屠殺”這個詞匯才第一次出現在《紐約時報》。1960年對阿道夫·艾希曼的逮捕以及1961年在以色列對他進行的審判,首次吸引了全世界對六百萬被屠殺猶太人的關注。學者們一致認為1967年的“六日戰爭”在“大屠殺記憶”的構建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就像歐洲猶太人曾經面臨的絕境一樣,來自阿拉伯世界的聯合打壓使得以色列國家的存亡危在旦夕。猶太民族這一次選擇先發制人,在戰爭爆發六天后就以絕對優勢控制了約旦河和尼羅河沿岸地區,重新接管了耶路撒冷,使得猶太人再次站在神圣的第二圣殿西墻土地上。
除此之外,還有兩個因素對于“大屠殺記憶”的美國化至關重要。首先,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美國社會開始主張少數民族的身份和權利。在這種趨勢的推動下,美國各地的大學和學院紛紛成立了各種各樣的種族研究中心。在此推動下,有關“大屠殺”研究的課程逐漸增多,吸引了很多學生的關注。其次,在1967年“六日戰爭”后,美國猶太人開始思考自身“犧牲和救贖”的問題。歐洲猶太人淪為大屠殺的犧牲品,而以色列和美國使他們得到救贖。美國在1973年的“贖罪日戰爭”中再次扮演了救贖者的角色。
在以色列軍隊遭受了空前的打擊、形勢十萬危急之時,美國通過空運物資直接干預了戰爭走勢。這對以色列和美國的“大屠殺記憶”產生了深遠影響。1977年以色列人民開始支持高舉民族主義大旗的利庫德集團并選舉梅納赫姆·貝京為總理,他一直致力于在增強實力、抵抗和利益的基礎之上構建猶太民族的身份認同感。在美國,越來越多的猶太人將以色列放在“大屠殺和救贖”敘事的中心位置,它作為被消滅的六百萬猶太人的救贖地,保證以色列的生存是必要的職責。“大屠殺記憶”成為美國猶太社區和以色列國家締結契約的基礎。
媒體在塑造美國化“大屠殺記憶”并傳播到猶太社區之外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除了同一時期反映納粹大屠殺的電影之外,1978年4月16號總時長達九個半小時的電視系列劇《大屠殺》在美國上演,1200萬觀眾通過節目對德國猶太人韋斯一家的悲慘遭遇感同身受。報紙對此進行了專題報道,分發學習指南給觀眾,猶太人在觀看節目時紛紛佩戴黃色“大衛之星”。節目產生的深遠影響也引起了政府的關注,在電視劇播出后不到兩周的時間,時任美國總統的卡特就在5月1日宣布成立紀念“大屠殺”總統委員會,以色列總理貝京和大約一千名“拉比”參加了委員會成立慶典活動。
暫且不提卡特總統這一公告背后的政治目的,委員會的成立使得“大屠殺記憶”在美國意識形態認同層面上得到規制,而位于華盛頓特區的美國大屠殺紀念館也在1993年落成并對公眾開放。紀念館是為了“悼念被納粹殺害的六百萬猶太人和幾百萬非猶太人”,它旨在呈現出大屠殺的真相,盡可能清晰而全面地告訴美國民眾在那段黑暗歲月發生的故事,使得公眾警醒“作為袖手旁觀者無意間犯下的罪行”。紀念大屠殺的另外一部電影《辛德勒的名單》也在當年熱映,總統克林頓和脫口秀名人奧普拉等人紛紛號召民眾走進影院去反思那段歷史。“大屠殺記憶”及其象征意義被建構成獨特的美國文化符號,這一過程是官方話語權、社會趨勢和大眾媒介相互作用的結果。
三、結語
導演斯皮爾伯格在介紹拍攝花絮時提到:“《拯救大兵瑞恩》是為了退伍軍人而拍攝的……如果沒有他們,我們也不會過上想要的生活。”電影不斷探討“怎樣在如煉獄般的戰爭中保持尊嚴”,角色霍瓦特對此做出了回答,“拯救列兵瑞恩也許是這場戰爭中唯一得體的事情”。這種對尊嚴、文明、人權的渴望通過角色傳達給了觀眾。“大屠殺記憶“逐漸走出美國的猶太社區,在社會民族身份認同中開始扮演重要角色。從殖民地時期走過的美國基督教價值體系將清白、自省、犧牲、受難以及拯救作為民族身份認同的基礎。這些準則是世俗盟約,也是國家統一和人民忠誠的源泉。
在電影中使用“大屠殺記憶”重新強調了民眾的國家認同感。從希特勒青年軍刀成為安息日面包刀,從心照不宣的目光對視到霍瓦特背包里裝滿沙土貼好標簽的錫罐,世俗盟約被一一踐行。斯皮爾伯格在電影中賦予了尋找列兵和諾曼底勝利登陸同樣重要的意義。觀眾無需解釋就能明白為什么要不惜一切代價猛攻奧馬哈海灘,也逐漸理解了八位士兵去拯救列兵瑞恩的重要性。在大屠殺的語境下,肯定個體生命的重要性是最有力的行動。
此外,將“大屠殺記憶”糅合進電影《拯救大兵瑞恩》中,使得過去的歷史成為未來道德準則的來源。文學評論家蒂姆·伍德(TimWood)在1998年寫道:“敘事模式在被用來構建道德歷史時會發揮一種功能,在集體記憶的治療實踐中遭遇’不可控制的他者’。”《拯救大兵瑞恩》就是這樣一種敘事模式,觀眾在電影里面遭遇的“他者”顯而易見是納粹暴行的噩夢,然而過去的歷史也是“不可控制的他者”。這些因素成為民族身份認同的道德瑕疵,也是大屠殺“記憶景觀”的一部分。電影將這種敘事模式下的美國道德正義置于無可指責之下:無論這個國家的缺點是什么,至少在人類生死存亡時刻它采取了行動,與納粹勢力展開了艱苦的斗爭。因此,斯皮爾伯格將“大屠殺記憶”編織進美國的文化記憶中,向那些為了終結戰爭的恐怖而犧牲的人致敬。
參考文獻:
[1]DaliaOfer.Israel[C]//DavidWyman,ed.TheWorldReactstotheHolocaust;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1996:836-922.
[2]DaliaOfer.WeIsraelisRemember,ButHow?TheMemoryoftheHolocaustandtheIsraeliExperience[J].IsraelStudies,2013(2):70-85.
文史論文投稿刊物:《文史博覽》(理論)是由致力于理論研究和關心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研究成果,人民政協的理論探索和履行職能新鮮經驗的研究成果,介紹評析中外學術界最新發展動態、觀點和論著的文稿。
轉載請注明來自發表學術論文網:http://www.zpfmc.com/wslw/2263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