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 要 預設是指以交際雙方的共同背景(共享的知識或信念)為前提的、聽話者根據(jù)特定語言標記(觸發(fā)標記)及其限定的對象(計算內容)而推理出的非外顯意義。例如, 張明又觸發(fā)標記發(fā)表了論文計算內容引發(fā)了張明之前發(fā)表過論文的預設推論。理解者依賴觸發(fā)標記通達交際雙方的共
摘 要 預設是指以交際雙方的共同背景(共享的知識或信念)為前提的、聽話者根據(jù)特定語言標記(觸發(fā)標記)及其限定的對象(計算內容)而推理出的非外顯意義。例如, “張明又觸發(fā)標記發(fā)表了論文計算內容”引發(fā)了“張明之前發(fā)表過論文”的預設推論。理解者依賴觸發(fā)標記通達交際雙方的共同背景, 并在計算內容上生成完整的預設; 隨后, 理解者連接生成的預設和共同背景, 更新兩者之間的關系。觸發(fā)標記范疇、共同背景與預設的關聯(lián)度、共同背景類型, 以及理解者的參與動機會影響不同階段的預設加工。未來研究可以從三個角度進一步探討預設加工的認知基礎:(1)采用計算建模的方法, 量化交際互動中聽話者理解預設的過程(如觀點采擇); (2)采用腦成像技術,揭示預設加工過程的神經基礎; (3)以特殊人群為研究對象, 檢驗和修正預設加工的認知模型。
關鍵詞 語用推理, 非外顯意義, 預設, 理性言語行為模型, 得體性, 觸發(fā)標記, 共同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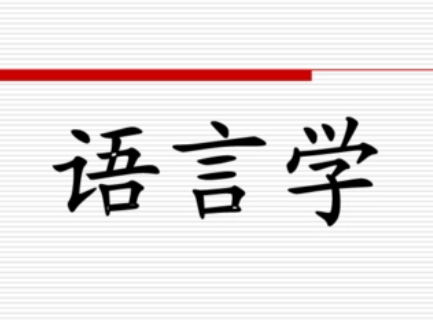
經濟性是語言交際過程的重要特征之一。說話者通常不明示交際雙方已知并共享的信息, 而是使用一些語言標記來提示這些信息, 從而提升語言交際的經濟性(Degen et al., 2020)。為此,語言學家 ( 特別是語用學家 ) 提出了 “ 預 設(presupposition)”這一概念, 用以區(qū)別不同層面的外顯和非外顯意義。預設是指以交際雙方的共同背景(common ground; Stalnaker, 2002)為前提的、聽話者根據(jù)特定語言標記(觸發(fā)標記)及其限定的對象(計算內容)而推理出的非外顯意義。共同背景指的是交際雙方共享的知識或者信念。理解者可以通過語言共現(xiàn)(linguistic co-presence, 即給理解者呈現(xiàn)的語言材料)、視覺共現(xiàn)(visual co-presence,即給理解者呈現(xiàn)的視覺場景)、一般性的世界知識(world knowledge)/社群關系(community membership,即通過社群形成的共識)等三種方式, 來建立交際雙方的共同背景(Clark & Marshall, 1981)。
例如,“張明又觸發(fā)標記發(fā)表了論文計算內容”中的“又”提示, 句子所描述的內容在過去已經發(fā)生過, 因此, “又”就是這個非外顯意義的預設觸發(fā)詞或觸發(fā)標記(trigger)。由于說話者不是外顯地給出這種已知并共享的信息, 因此預設內容具有隱含性; 聽話者需要推理出預設信息, 并將之與共同背景進行關聯(lián)和比較。這就使得預設理解具有語境依賴性;在理解過程中, 聽話者需要兼顧說話者和自己視角內的背景信息。研究者按照不同的語義范疇,將預設觸發(fā)標記劃分為定指范疇(如“這個”)、反預期范疇(如“連…都”)、敘實范疇(如“知道”)、狀態(tài)改變范疇(如“停止”)、焦點范疇(如“僅”)、重復范疇(如“又”)等。不同語義范疇具有跨語言的普遍性,所以預設的觸發(fā)標記范疇類型很可能普遍存在于不同語言內 , 比 如 “這 個 ”和 “the”。
計算內容(computational point, 如“論文”)是句子中的關鍵詞或短語, 可以使聽話者知曉說話者預設的內容。聽話者從觸發(fā)標記推理出相應的語義范疇,并期待隨后出現(xiàn)的計算內容滿足該語義范疇, 以實現(xiàn)語言的經濟性。總之, “張明又發(fā)表了論文”引發(fā)了“在此之前, 張明發(fā)表過論文”的預設推論(即非外顯意義)1, 而這種預設推論屬于交際雙方共同背景中的已知信息。
以往語言哲學、語用學和心理語言學從不同維度探討過預設問題。一方面, 語言哲學中的意義理論(探討如何從語句中獲得意義, meaning)認為, 預設、含義(implicature)、句子的規(guī)約意義(conventional meaning)及所述內容(what is said)或斷言(assertion)共同構成了語言交流意義的四個層面(陳嘉映, 2003; Domaneschi, 2016)。其中, 句子的規(guī)約意義和所述內容(或斷言)為說話者外顯表達的意義, 一般不受語境的影響; 而預設和含義則為說話者沒有外顯表達的信息。預設與含義的區(qū)別在于, 前者是在特定語境下聽話者可以推理出的交際雙方已知和共享的信息; 后者是聽話者推理出的未知信息(Domaneschi, 2016; 蔣曉鳴,周曉林, 2013)。
另一方面, 語用學和心理語言學往往將預設的不同范疇放在不同的語用加工問題中(如定指、焦點、構式結構加工)進行研究, 這種做法使得研究者對預設加工難以形成整體性的認知。下文將梳理和整合有關預設的研究成果, 以期還原預設加工的整體面貌。當前有關語言交際的認知模型有一個尚待考慮的重要問題(魏在江, 2014; Schwarz, 2014), 即聽話者的大腦如何從這些習慣化的、有限的語言標記中提取出說話者的預設(即“預設生成”), 并將預設整合到上下文語境(或世界知識)中(即“預設的得體性加工”2, presupposition felicity processing)。下文將闡述預設生成與得體性加工這兩個認知階段, 分析共同背景在兩類語言標記(即觸發(fā)標記和計算內容)上的作用; 本文還將根據(jù)預設加工的不同階段, 分析觸發(fā)標記范疇、共同背景與預設內容的關聯(lián)度、不同類型的共同背景、以及被試參與動機的影響與作用。在此基礎上, 本文將進一步提出, 未來至少可以從計算模型、神經基礎和個體差異等三個角度來探討交際與語篇任務中預設理解的認知加工機制。
1 預設的加工階段
以往有關預設加工過程的研究主要涉及焦點詞(如 only)、構式結構(如漢語“連…都”結構)、特指詞(如 the)、銜接詞(如 again)等觸發(fā)標記。這些預設觸發(fā)標記從句法功能角度將上下文語境與當前語言材料聯(lián)系起來, 以供理解者生成預設; 隨后, 理解者將生成的預設與上下文語境進行關聯(lián),并更新兩者之間的關系(即進行“得體性加工”)。其中涉及的重要問題是, 預設理解是如何受到上下文語境的制約?即理解者是按照默認方式(defaultprocessing, 即預設是默認狀態(tài)下的推理結果, 會自發(fā)產生)進行預設加工?還是需要努力提取語言之外的語用信息來幫助理解?這些重要問題都提示我們, 有必要對預設的加工過程進行梳理。
1.1 預設生成
預設的生成是理解預設的前提步驟, 由觸發(fā)標記及計算內容共同決定(Tiemann et al., 2011)。觸發(fā)標記提醒理解者依據(jù)當前語境中出現(xiàn)的信息進行檢索, 或者對語境中未出現(xiàn)的信息進行推理。觸發(fā)標記也規(guī)定了交際情景是如何限定計算內容的 ( 這些過程被稱為預設的觸發(fā)機制 ,Tiemann et al., 2011, 實驗一)。通常, 計算內容是觸發(fā)標記所指向的對象(預設的對象可能是動作、人或事等), 但并不是預設生成的關鍵要素。在聽到觸發(fā)標記時(如“張明沒有還清觸發(fā)標記 …”), 理解者可能會根據(jù)上下文語境(“去年, 張明向李四借錢”)來主動預期計算內容(“李四的錢”), 以生成完整的預設。因此, 預設的生成會受到語境及個體知識背景等因素的影響 (Jiang & Zhou, 2020;Pickering & Garrod, 2007; Schneider et al., 2021)。換言之, 即使預設的計算內容沒有在當前語言材料中展現(xiàn), 理解者也可以根據(jù)相關的共同背景與觸發(fā)標記來生成預設。由于共同背景和觸發(fā)標記之間存在某種照應聯(lián)系, 因此語境對觸發(fā)標記的影響機制可能符合語言中句子成分依存關系的某些特性3(張亞旭 等, 2007; Wang & Schumacher,2013; Nieuwland & Martin, 2017; Coopmans &Nieuwland, 2020)。同樣, 若觸發(fā)標記位于計算內容之后, 預設生成也可能會發(fā)生在觸發(fā)標記上。預設生成還可能會受到語序靈活性的影響。
1.2 預設內容的核證與得體性加工
在預設生成后, 理解者需要在計算內容上核證生成的預設與語境(或共同背景)之間的關系。若話語中觸發(fā)標記的位置在計算內容之后, 理解者則會在觸發(fā)標記上核證這種關系。預設內容的核證階段即是預設得體性加工, 它是指在觸發(fā)標記與計算內容共同生成完整預設時, 理解者將連接生成的預設與上下文語境, 并更新兩者之間的關系的過程(Schwarz, 2016)。根據(jù)預設內容與共同背景之間的匹配關系, 研究者將預設得體性分為預設滿足和預設違反兩種水平。
2 共同背景在預設加工中的作用
在明晰預設加工的兩個階段后, 本文此處關注預設加工的核心因素:共同背景。尚不清楚的是, 共同背景在什么時候起作用?是影響觸發(fā)標記加工, 還是影響計算內容加工?一種觀點認為,共同背景對預設加工階段的影響始于觸發(fā)標記(Schwarz, 2014)。相關研究對比了不同預設句(預設滿足句、預設違反句、預設調補句)和斷言句在觸發(fā)標記上的加工差異。斷言句是指用于表達個人知識、觀點、主張、態(tài)度的句子, 它沒有外顯觸發(fā)標記, 且承載的信息為新信息(如“一個非定指詞小伙子在喝茶”)。預設句則需要依賴觸發(fā)標記與計算內容, 它有明確的外顯觸發(fā)標記, 且承載的信息為舊信息(如“這個定指詞小伙子在喝茶”), 同時還受制于上文語境或者共同背景。另一種觀點則認 為 , 共同背景在完整的預設生成時起作用(Domaneschi et al., 2018)。
一些研究因此比較了不同預設句(預設滿足句、預設違反句、預設調補句)和斷言句在計算內容上的加工差異。兩種觀點的核心爭論在于, 共同背景起作用的時間是在完整預設生成之前, 還是生成之時。
2.1 共同背景對預設加工的影響
或始于觸發(fā)標記觸發(fā)標記是預設生成的核心要素, 可以引發(fā)語義預設(由詞語誘發(fā)的語義信息)。為探討共同背景是否在觸發(fā)標記上施加影響, 研究者將預設句與具有相似意義的斷言句進行對比。早期的研究者讓兩批被試分別閱讀包含定指詞(the 觸發(fā)標記)或非定指詞(a 非觸發(fā)標記)的文本, 結果發(fā)現(xiàn), 被試閱讀帶有定指詞文本的時間較短。這似乎表明, 相比預設滿足句 , 加工斷言句需要更多的認知努力(Murphy, 1984)。在加工帶有定指詞的文本時, 理解者只需要提取以往信息的相關內容, 而加工含有非定指詞的文本時, 則需要建立新的心理表征。因此, 預設的生成可能促進了理解者對句子整體的閱讀理解(Schneider et al., 2020; Schneider& Janczyk, 2020)。
但在 Murphy (1984)研究中, 兩種條件之間的差異還可能由關鍵句的語義信息不匹配造成。近期的研究(如 Schneider et al., 2019)采用鼠標追蹤范式(mouse-tracking paradigm)4, 探討了共同背景如何影響含有定指詞語句與含有非定指詞語句的加工代價。在鼠標追蹤范式中, 理解者在看到語句(定指句或非定指句)的同時, 需要把鼠標移動到備選圖片區(qū)域(在這個實驗中, 共同背景通過視覺圖片來呈現(xiàn))。結果發(fā)現(xiàn), 相比定指詞條件, 非定指詞條件的鼠標移動時間更長,表明非定指詞條件的加工代價更高。但該研究沒有報告理解者在每個詞語上的鼠標移動時間, 無法揭示共同背景在觸發(fā)標記上的即時效應。
研究者進一步采用“視覺情景范式” (visualworld paradigm)和眼球追蹤技術, 考察重復范疇預設(“again”)與斷言(“twice”)在即時加工過程中的差異(Schwarz, 2014)。視覺陣列中呈現(xiàn)兩種圖片類型, 分別為目標圖片(如, 周一“打高爾夫球”,周二“踢足球”, 周四“打高爾夫球”)和競爭圖片(如, 周一和周二均“打排球”, 周四“打高爾夫球”)。理解者看完屏幕上同時呈現(xiàn)的兩種圖片后,首先聽語境句(“Some of these children went toplay golf on Monday, and some to play volleyball.”),接著聽預設句(“John went to play golf (i) again 觸發(fā)標記later on...”)或者斷言句(“John went to play golf (ii)twice this week...”) 。
結果發(fā)現(xiàn) , 從 “again” 或“twice”呈現(xiàn) 200 ms 后(200~400 ms), 理解者在目標圖片上的注視比例顯著高于競爭圖片; 這是因為“again”或“twice”引發(fā)的語義信息與競爭圖片呈現(xiàn)的信息不一致。這表明, 共同背景(即視覺圖片中是否包含預設滿足的共同背景)在預設觸發(fā)標記上的作用即時。但兩種句子(預設句和斷言句)之間的注視比例差異不顯著, 這與之前的研究結論相左(Tiemann et al., 2011), 可能是由于兩個實驗設計的差異。當前研究中, 無論是加工“again”還是加工“twice”, 被試對事件數(shù)量進行計算的結果都相同。因此, 在嚴格控制預設句與斷言句的語義關系之后, 預設句與斷言句加工因為某些情況下關鍵詞之間的語義相似性, 可能表現(xiàn)出相同的認知過程。
總之, 來自不同實驗的結果表明, 共同背景在預設觸發(fā)標記上的作用即時發(fā)生。但預設觸發(fā)標記與非觸發(fā)標記的加工之間是否存在差異, 目前還沒有一致的結論。有研究發(fā)現(xiàn), 觸發(fā)標記比非觸發(fā)標記加工更容易(Murphy, 1984; Schneideret al., 2019); 另外一些研究發(fā)現(xiàn), 觸發(fā)標記比非觸發(fā)標記的加工難度更高(Tiemann et al., 2011);還有研究認為, 兩者之間沒有顯著差異(Schwarz,2014)。仔細分析各項研究, 可以發(fā)現(xiàn), 結論的不一致有可能是因為研究者采用了不同的句子類型。比如, Murphy (1984)采用的是預設滿足句, 即語境中提供的共同背景與生成的預設匹配; 而Tiemann 等(2011)采用的是預設違反句, 即語境中提供的共同背景與生成的預設不匹配。此時, 理解者需要處理共同背景與生成預設之間的不一致;而在斷言句中, 理解者需要將斷言句中的新信息整合至已有的心理模型中。
相應的實驗結果表明,預設滿足句中的共同背景促進觸發(fā)標記的加工,而預設違反句中的共同背景阻礙觸發(fā)標記的加工。相比前面的研究, Schwarz (2014)進一步控制了預設句中的觸發(fā)標記與斷言句的非觸發(fā)標記的語義一致性。結果發(fā)現(xiàn), 共同背景不能區(qū)分觸發(fā)標記與非觸發(fā)標記的加工。未來需要設計更加精巧的實驗, 來回答預設句與斷言句的加工之間是否存在差異。
2.2 共同背景對預設內容的核證過程影響
體現(xiàn)在計算內容上在預設生成時, 理解者需要在計算內容上對預設內容進行核證(如前所述, 主要包括連接和更新兩個階段)。一些研究比較了預設違反句和斷言句、預設調補句和斷言句, 以及預設滿足句和預設調補句在計算內容上的加工差異。例如, Clifton(2013)采用自定步速逐詞閱讀任務, 考察預設違反句與斷言句的加工差異。被試的任務是分屏閱讀句子 (如 “In the kitchen, /Jason checked out/[the/a]觸發(fā)標記/非觸發(fā)標記 stove 計算內容/ very carefully.”),之后完成干擾任務(簡單的數(shù)學加減任務), 再回答相關問題(如“Jason was checking out somethingthat he could cook with /that he could clean with.”)。
雖然在觸發(fā)標記與計算內容這一屏上, 定指詞(thestove)與非定指詞(a stove)的閱讀時間沒有顯著性差異, 但在計算內容后一屏短語(very carefully)上,當語境中出現(xiàn)單個指稱物時, 含有定指詞條件(預設)比含有非定指詞條件(斷言)的閱讀時間更快;當語境中出現(xiàn)多個指稱物時, 含有定指詞條件相比含有非定指詞條件的閱讀時間更慢, 這可能是因為被試需要從多個指稱物中進行解歧。這種效應的延遲現(xiàn)象, 即在關鍵詞后一屏觀察到效應,經常出現(xiàn)在自定步速閱讀實驗中(Mitchell, 2004)。由于沒有分別記錄“the/a”和“stove”的閱讀時間,研究者難以確定語境施加的影響是表現(xiàn)在在觸發(fā)標記上, 還是在計算內容上。
3 預設認知加工過程的影響因素
預設加工的不同階段受到諸多因素的制約。比如, 在預設生成和得體性加工這兩個階段, 不同范疇的預設觸發(fā)標記施加的影響可能不同; 在預設得體性加工階段, 預設與共同背景信息之間的語義關聯(lián)程度可能調節(jié)預設得體性的加工; 不同類型的共同背景可能導致理解者使用不同的加工機制來處理預設; 在人際互動過程中, 被試參與實驗任務的動機可能會調節(jié)預設加工的深度,如此等等。
3.1 觸發(fā)標記范疇預設的生成與得體性的加工均受制于觸發(fā)標記。預設觸發(fā)標記范疇的劃分在語用學/語義學上一直存在爭議(Abusch, 2010; Domaneschi et al.,2014; Glanzberg, 2005)。語言學家往往按預設觸發(fā)標記的語義范疇(如定指范疇、敘實范疇和重復范疇等), 或者按照觸發(fā)標記的形態(tài)凸顯度來分類。比如, 有些詞通常以附屬標記的形式與實詞共同出現(xiàn)(如“還清”中的“清”), 這類標記必須與動詞一起來觸發(fā)預設; 而另一些詞(如“又”)可以以詞匯形式單獨出現(xiàn), 獨立觸發(fā)預設。Abusch (2010)根據(jù)預設生成是否對語境敏感, 將觸發(fā)標記區(qū)分為軟預設觸發(fā)標記(soft presupposition trigger, 如“Tom continues 觸發(fā)標記 to go to school.”)和硬預設觸發(fā)標記(hard presupposition trigger, 如“Tom waslate again 觸發(fā)標記.”)。
兩者的差異在于預設生成在多大程度上依賴語境; 相比硬觸發(fā)標記, 軟觸發(fā)標記更加依賴語境。Glanzberg (2005)根據(jù)預設匹配失敗后, 理解者是否有必要調補, 將觸發(fā)標記分為弱預設觸發(fā)標記(weak trigger, 如“John solvedthe problem too 觸發(fā)標記.”)和強預設觸發(fā)標記(strongtrigger, 如“John regrets 觸發(fā)標記 voting for Bush.”)。當判斷預設與語境的整合關系為不得體時, 由弱觸發(fā)標記誘發(fā)的預設句, 理解者可以選擇是否調補; 由強觸發(fā)標記誘發(fā)的預設句, 理解者必須進行調補。強弱標記可能反映了預設內容在靈活性和必要性上的差異。
3.2不同類型的共同背景
前文主要關注了共同背景在觸發(fā)標記和計算內容上的即時性加工(見第 2 部分), 分析了共同背景與預設的語義關聯(lián)度如何調節(jié)預設的得體性加工(見第 3.2 部分)。在本節(jié)中, 我們闡述不同共同背景類型在預設加工過程中的作用。預設理解對共同背景類型具有高度依賴性。過去的研究在不同實驗中操作了三種共同背景類型, 比如語言共現(xiàn)(Domaneschi & Paola, 2018;Burkhardt, 2006)、視覺共現(xiàn)(Schwarz, 2014; Schneideret al., 2019), 以及世界知識/社群關系(Jiang et al.,2013; Zang et al., 2019)。語言共現(xiàn)是指聽話者從給定的語言材料中獲取與當前任務相關的背景信息; 視覺共現(xiàn)是指聽話者從對話場景中的視覺信息獲取與當前任務相關的背景信息。兩者的主要區(qū)別在于聽話者獲取背景信息的來源和方式(Galati & Brennan, 2021)。
在實驗任務中, 對于語言共現(xiàn)和視覺共現(xiàn), 聽話者一般是從短時記憶或者工作記憶中提取背景信息; 世界知識或者社群關系則是指聽話者從長時記憶中提取相關的背景信息。因此, 前兩者與后一類的主要區(qū)別在于背景信息在大腦中保持時間的長短(van Moort et al.,2020; van Moort et al., 2018, 2021)。例如, Jiang 等(2013)對漢語中“連(A)…都(B)”結構攜帶的預設進行考察。該結構引發(fā)的預設為:根據(jù)個人的世界知識, A 實施 B 的可能性較低。結果發(fā)現(xiàn), 預設違反(“*連這么大的聲音章宏都能聽清楚, 太敏銳了”)較預設滿足(“連這么小的聲音章宏都觸發(fā)標記能聽清楚, 太敏銳了”)在關鍵詞“聽清楚”上誘發(fā)了更大的 N400 波幅(350~450 ms)和更大的晚期負活動(550~800 ms)。N400 效應說明, 在預設違反條件下, 語境中的高可能性事件和“連…都”結構觸發(fā)的預設在整合時會產生較大的困難。晚期負活動可能反映, 理解者基于“連…都”結構的預設,對事件的合理性進行重新調整或推理(如, 認為章宏可能聽力本來就不好)。
4 研究展望
基于以往研究對預設加工過程與其背后關鍵性因素的探討, 未來研究可以(1)基于已有計算模型(如基于貝葉斯的理性言語行為模型)對預設使用者與理解者雙方的心理過程進行量化建模, (2)揭示預設加工的神經基礎, 以及(3)以特殊人群為研究對象, 檢驗和修正預設加工的認知模型等方面繼續(xù)探討。
4.1 基于預設理解的計算
建模傳統(tǒng)實驗設計通常根據(jù)語言理解或產生的結果, 來推理交際雙方的認知過程(如視角采擇),而貝葉斯模型在量化說話者或聽話者的心理模擬過程方面具有明顯優(yōu)勢。理性言語行為模型(rational speech act model)認為, 在交際過程中,說話者與聽話者均秉承合作原則傳遞言語中的預設, 即說話者在產出預設時, 需要考慮雙方的共同背景, 并推理聽話者能否通過觸發(fā)標記解碼預設內容; 聽話者在理解說話者的預設時, 會主動識別觸發(fā)標記, 并據(jù)此推理說話者的預設目的(Degen et al., 2020; Frank & Goodman, 2012; Mi etal., 2021)。基于貝葉斯的理性言語行為模型可以對交際雙方的認知過程變化進行預測和計算建模。貝葉斯模型還能綜合考慮個體在實驗以外形成的知識經驗等因素(Holler & Levinson, 2019;蔣曉鳴, 2020), 實施認知計算。
因此, 相比傳統(tǒng)實驗設計, 貝葉斯模型可以解釋更多的數(shù)據(jù)變異。以聽話者理解模型為例, 在預設理解的貝葉斯計算建模過程中, 研究者需要確定先驗概率、似然比及后驗概率的心理意義或者心理過程。先驗概率 P (S)是聽話者進行交流之前的、受個體經驗影響的預設使用概率或預設在共同背景中的凸顯概率; 似然比 P (D|S)是理性言語行為模型的核心, 在假定說話者秉承合作原則的條件下, 聽話者模擬說話者產出預設的心理過程, 即說話者為傳遞預設而選擇某些預設觸發(fā)標記及計算內容的概率; 后驗概率 P (S|D)可以視為聽話者接收到說話者的語言材料時, 成功恢復說話者試圖傳遞預設的概率(Frank & Goodman, 2012)。相比先驗概率, 似然比可能受到個體語用能力(或觀點采擇能力)的影響。例如, 低觀點采擇能力與高觀點采擇能力的個體在模擬說話者產出預設過程的程度上存在差異(Franke & Degen, 2016)。個體的工作記憶更新能力(Yang et al., 2018; Yang et al., 2020;Zhang et al., 2021)、言語和非言語推理能力亦會影響似然比。未來研究可根據(jù)基于貝葉斯的理性言語行為模型, 來探討預設加工過程及其影響因素。
以往研究主要以健康被試為研究對象, 探討了預設加工的認知過程; 但以特殊人群(如自閉癥人群)為研究對象, 亦能幫助研究者檢驗并修正預設加工過程的模型。有關哪些個體差異因素能夠預測不同人群預設加工的認知神經機制, 還需要基于健康人群建立預設認知模型, 并在特殊人群中檢驗其預測的有效性。一些研究發(fā)現(xiàn), 在控制一般語言能力和非語言智力后, 自閉癥兒童在理解帶預設觸發(fā)標記的問題方面比正常兒童表現(xiàn)更差。組別與觸發(fā)標記范疇之間沒有交互作用。該結果提示, 自閉癥兒童在理解預設問題時的困難可能表現(xiàn)出不同觸發(fā)標記范疇間的普遍性(Cheung et al., 2017; Cheung et al., 2020)。
由于缺乏斷言條件的控制組, 也沒有記錄反應時, 我們無法確定, 以往研究中兩組被試在預設理解問題上的差異體現(xiàn)在生成階段, 還是核證階段?這種差異是反映了語篇連接過程, 還是語篇更新過程(An et al., 2020)?此外, 自閉癥譜系障礙在加工預設時可能受到自閉譜系商數(shù)量表的子維度(如,注意細節(jié)、注意切換、想象、社交技巧以及交流)的影響。根據(jù)自閉癥的特點, 我們預測:在語篇閱讀任務中, “注意細節(jié)”的特質可能會造成自閉癥兒童在語篇連接和更新階段不同于正常兒童;在交際互動任務中, 自閉癥兒童在利用他人視角理解預設信息時的表現(xiàn)可能不如正常兒童。未來研究可以將基于健康人群數(shù)據(jù)建立的個體差異預測模型用在特殊人群數(shù)據(jù)上, 開展檢驗, 以修正健康人群中得到的模型。
參考文獻:
陳嘉映. (2003). 語言哲學. 北京大學出版社.蔣曉鳴. (2020). 文化互鑒視角下非言語表情的嗓音編碼和解碼. 同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31(1), 116–124.
蔣曉鳴, 周曉林. (2013). 語用等級含義加工的腦與認知機制. 語言學研究, (2), 32–42.隋雪, 史漢文, 李雨桐. (2021).
語言加工過程中的觀點采擇及其認知機制. 心理科學進展, 29(6), 990–999.魏在江. (2014). 語用預設的認知語用研究. 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張亞旭, 蔣曉鳴, 黃永靜. (2007).
言語工作記憶, 句子理解與句法依存關系加工. 心理科學進展, 15(01), 22–28.Abusch, D. (2010).
Presupposition triggering from alternatives.Journal of Semantics, 27(1), 37–80.An, S., Bill, C., & Yang, Q. (2020). Comprehension of thepresupposition trigger Ye “Also” by mandarin-speakingpreschoolers with and without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1, 570453.
Brown-Schmidt, S., Gunlogson, C., & Tanenhaus, M. K. (2008).Addressees distinguish shared from private informationwhen interpreting questions during interactive conversation.Cognition, 107(3), 1122–1134.Brown-Schmidt, S., & Heller, D. (2018).
Perspective-takingduring conversation. In S. Rueschemeyer & M. G. Gaskell(Eds.), Oxford Handbook of Psycholinguistics (2nd ed.)(pp. 551–57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Burkhardt, P. (2006).
Inferential bridging relations revealdistinct neural mechanisms: Evidence from event-relatedbrain potentials. Brain and Language, 98(2), 159–168.Cheung, C. C. H., Politzer-Ahles, S., Hwang, H., Chui, R. L.Y., Leung, M. T., & Tang, T. P. Y. (2017).
Comprehensionof presuppositions in school-age Cantonese-speaking childrenwith and without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Clinical Linguistics& Phonetics, 31(7-9), 557–572.
作者:楊 琪 1 蔣曉鳴 2 周曉林 2
轉載請注明來自發(fā)表學術論文網:http://www.zpfmc.com/jylw/3023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