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 要]幽靈批評也被稱為侵擾學。 它于 20 世紀八九十年代勃興,于本世紀初到當下發展繁盛,大有對今后幾十年的批評活動產生深遠影響的勢頭。 幽靈批評在初期主要是對文學作品中的鬼魂人物和互文現象等進行評論,在發展中與其他批評流派相交融,逐漸趨于系統化和理論化,同
[摘 要]“幽靈批評”也被稱為“侵擾學”。 它于 20 世紀八九十年代勃興,于本世紀初到當下發展繁盛,大有對今后幾十年的批評活動產生深遠影響的勢頭。 幽靈批評在初期主要是對文學作品中的鬼魂人物和互文現象等進行評論,在發展中與其他批評流派相交融,逐漸趨于系統化和“理論化”,同時把理論與批評實踐相結合,拓展研究邊界,豐富研究方法,最終發展成為一種綜合性強、生命力旺盛的文學批評潮流。 它的主要觀點集中在孤兒法則(The Law of the Orphan)、心理投射、集體記憶洞穴、在場(presence)與缺場(absence)之間的間性( in-betweenness)、多重敘事等方面,與現代精神分析、解構主義等存在著復雜的呼應和互動關系。 目前幽靈批評的研究對象大多為哥特文學、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文學、殖民和后殖民文學、流散文學等,研究范疇包括幽靈人物、人物間的幽靈關系、插曲間的幽靈關系、作者的潛意識、多重敘事、語言衍變等,研究內容大多涉及互文、暗恐、集體無意識、創傷、閱讀機制等方面,這些研究大多具有某些現實關注,具有政治性和倫理性。
[關鍵詞]幽靈批評;發展歷程;主要觀點;研究范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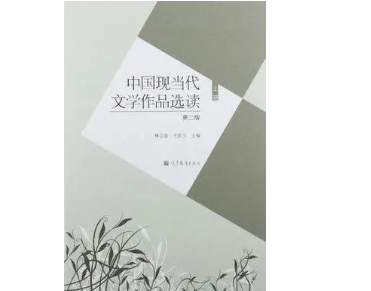
“幽靈批評”(spectral criticism)也被稱作“侵擾學”(hauntology)。 一般認為,“幽靈批評”勃興于 20世紀八九十年代,并于本世紀初至當下一直處于興盛狀態,逐漸成為顯學,并將會“對今后幾十年的批評活動繼續產生一種多少具有幽靈性質的影響”①。
幽靈批評雖然沒有明確固定的理論源起,但它最近幾十年的發展尚有大致的脈絡:它在初期主要是對文學作品中的鬼魂人物和互文現象等進行評論,在發展中逐漸趨于幽靈批評理論的系統化和“理論化”,到成熟期主要是有意識地把理論與批評實踐相結合,進一步凝練深化理論,拓展研究邊界、豐富研究方法,在發展中日漸與其他批評流派相交融,最終發展成為一種綜合性強、生命力旺盛的文學批評潮流。目前盡管有中外學者試圖總結幽靈批評的發展歷程、與其他理論的互動、研究范式等問題,但由于過于憚于幽靈批評理論與實踐的開放性,其研究的結論要么局限于對具體的批評實踐的梳理,要么滿足于哲學化的討論,對幽靈批評的主要觀點與研究范疇等問題語焉不詳。
例如幽靈批評的大家龐特(DavidPunter),在《幽靈批評》一文中梳理了不少幽靈批評實踐的著作,也談到了與幽靈批評相呼應的理論,至于幽靈批評的主要理論觀點與研究范疇,卻沒有較為明晰的說明總結。 而戴維斯(Colin Davis)的文章“État Présent: Hauntology,Spectres and Phantoms”,雖然論證了什么是侵擾學及幽靈的本質,但該文的論證過于簡略,其重點是討論幽靈批評的兩大流派的區別。
在國內,曾艷兵教授先后發表《“幽靈批評”與批評的“幽靈”》《關于“幽靈批評”的批評》兩篇文章。 前者介紹了龐特關于幽靈批評的論述,從互文性和文本與歷史的關系兩方面強調了文本的幽靈性,也指出了批評本體的幽靈性;后者對幽靈批評概述后分析了《奧德賽》《埃涅阿斯紀》《神曲》《哈姆雷特》等作品中的幽靈及它們的互文關系,認為“所有的名著都具有幽靈的性質,或者說經典總是一種幽靈事件。”①申富英、靳曉冉的《論幽靈批評的理論“淵源”、研究范式與發展趨勢》雖然較系統地梳理和評價了幽靈批評,但對其主要觀點與研究范疇未作系統研究。 不難看出,學界有必要對幽靈批評的主要觀點與研究范疇等作系統的梳理研究。
一、幽靈批評的發展歷程與其他任何批評理論一樣,幽靈批評的早期形態為批評實踐。 把幽靈批評中常常涉及的“鬼魂”作為文學研究對象來研究的最早作品之一是莎麗·本斯托克(Shari Benstock)的《作為鬼故事的〈尤利西斯〉》。 在該文中,她不僅探討了鬼魂的實質,而且還把鬼魂研究與心理學和結構主義哲學密切結合。以《尤利西斯》文本中的幽靈為研究對象,本斯托克探討了幽靈侵擾的原因、機制及美學效果。 雖然本斯托克未對幽靈下一個清晰的學術定義,但她對幽靈的本質頗有洞見。 在引用《尤利西斯》中斯蒂芬對鬼魂的定義———通過死亡、不在場和行為的改變而墮入無法觸及的狀態———之后,她馬上又補充說,“雖然[斯蒂芬]希望他的母親通過死亡墮入不可觸及的狀態,但她拒絕墮入這樣的狀態,就如她拒絕在斯蒂芬面前變成缺場一樣”②。
換言之,本斯托克借此說明了幽靈的本質是介于在場與不在場之間的存在,它不斷侵擾人的精神意識。 該文還指出,莎士比亞的鬼魂是斯蒂芬藝術思想和創作焦慮意識的投射;斯蒂芬母親的鬼魂是他對天主教的憤恨及對母親內疚情感的投射。 本斯托克認為,幽靈生成文本意義的不穩定性,但也增加了文本雙重敘事的張力。幽靈批評較早的實踐者還有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
在其《文學空間》中,作者未重點討論何為幽靈,但對人死之后的鬼魂關注較多。 布朗肖認為對于鬼魂的書寫是一種表現歷史對于當下、缺場對于在場的永遠揮之不去的影響的隱喻式書寫策略,這種影響是一種處于在場和不在場之間的間性存在,連凝視都“變成了一種永恒顯現的幽靈”③。 這句關于凝視的幽靈性的引文也成為后世評論各種政治規訓所造成的創傷時屢屢引用的名言。 該書還有另一貢獻:它探討閱讀行為的幽靈本質和歷史對閱讀行為本身的幽靈式影響———閱讀行為是一種與死者的對話,文本是死去的人的聲音回歸(侵擾)的場域。從理論層面正式探討幽靈的比較早的著作是本內特(Andrew Bennett)和羅伊爾(Nicholas Royle)的《文學批評:理論與實踐導論》一書。
該書專門設立一個章節討論“幽靈”,從這點而言,它在幽靈批評理論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 該書的貢獻是大體按時間順序對關于文學作品中的幽靈研究進行了學術史梳理,并把“幽靈”理解成文本之間所存在的一切關系的基質,是閱讀行為發生時所有意義鏈的不確定性總和,而這些不確定性是研究任何文本的基礎。 同時,該書為理解“幽靈”的本質提供了多種可能性嘗試,比如,幽靈就是歷史創傷的形象化表征;幽靈是一種心理投射,是深藏人類潛意識的暗恐。從批評實踐到理論、又從理論到批評實踐游刃有余、在理論層面將“幽靈批評”系統化的學者當屬龐特。
龐特是研究哥特文學的知名專家,他的相關批評實踐為他將幽靈理論系統化和體系化提供了基礎。 他首次提出“幽靈”的“孤兒法則”,并以哥特文學為例,強調無論在體裁還是母題上,文學根本沒有固定的來源或根源。 龐特的另一個貢獻就是他在梳理幽靈批評的發展史的同時也暗示了它的研究范疇和主要研究范式。 既然所有的不穩定性、流動性和間質性存在都可成為幽靈,那么幽靈批評的研究范疇也就包括文本內外的對文本生成意義產生影響的一切不確定性元素。
龐特對幽靈批評的范疇的厘清有兩個特點,一是間接性,即他并未明確地對幽靈批評的范疇進行界定;二是他在間接勾勒這個范疇時以文本意義的生成為焦點。幽靈批評理論在逐漸系統化的過程中也不乏內部的理論之爭,尤其是關于幽靈的秘密是否可以被揭示的論爭。 戴維斯對幽靈批評的倫理內涵以及幽靈批評內部分歧性問題進行了研究。 他更傾向于用“侵擾學”來指代“幽靈批評”,認為侵擾學更能體現幽靈的影響力。 他認為,在幽靈研究方面,德里達的信徒和托羅克(Maria Torok)的信徒存在較大的分歧,而雙方的異見對于幽靈批評的實踐者們而言意義重大。 德里達(Jacques Derrida)強調幽靈秘密的不確定性:它是隱藏在我們認為我們所知之中的同時又能從根基上破壞我們認知的一種本質的無知性,昭示著“意義開放性生產”的可能性①。
而托羅克的信徒們認為,對一無所知的后代們的生活進行反復侵擾的前輩們的隱秘創傷“是個撒謊者,它侵擾的目的是刻意誤導被侵擾的主體,確保它的秘密一直處于隱秘之中”②。 對文學作品的幽靈批評就是去揭示這樣的秘密,盡管此類秘密抗拒被揭示,但內在地具有被揭示的可能性。 兩派的分歧實際上為幽靈批評的實踐提出了必須思考的問題,即在使用幽靈批評時需在多大程度上保持討論的開放性,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保持觀點和結論的確定性和肯定性。 幽靈批評理論的內部分歧也從側面彰顯了幽靈批評的學術價值,即“侵擾學是加強文學研究的某種嘗試,它使文學研究成為拷問我們與死者關系、審視生者流動性身份及探討思想和無思邊界的場域。 鬼魂變成了認識論和倫理學范疇矛盾立場的交匯點”③。
二、幽靈批評的主要觀點
與其他許多批評流派不同,幽靈批評沒有清晰的理論源頭,但卻有與現當代其他文論相呼應的理論觀點。 換句話說,幽靈批評的理論觀點從某種程度上說是在對文學中的幽靈及幽靈元素研究方面與其他理論對話和互鑒,并在這種對話和互鑒中逐漸明晰自己的思想觀點。首先,幽靈批評理論對幽靈的本質進行了界定。 幽靈批評理論認為,幽靈是介于在場與不在場之間的間質性存在,它具有在現實界無法抓住或觸摸但會持續留下印記的特點,具有夢幻、幻覺、魔幻或幻想等神秘色彩;幽靈具有與宗教類似的作用,令人陷入欲罷不能的迷狂狀態,它不斷侵擾人類的精神領域,且與語言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幽靈是與人的精神,或者說,與可以使人成其為人的靈魂相關:“幽靈是我們關于人的思考中的根本性的東西,也就是說,成為人即意味著擁有一種精神,一種靈魂,或一種幽靈。”④
在幽靈批評者的眼中,幽靈的本質帶有解構主義的底色。 幽靈批評主要研究的三個方面,即幽靈的不確定性和間性、幽靈的心理投射特點以及幽靈批評的解構主義本質,均與幽靈的定義密切相關。幽靈批評者們對幽靈的定義與德里達的《馬克思的幽靈》具有千絲萬縷的聯系。
雖然德里達并不是幽靈批評的創始人,但他在《馬克思的幽靈》中對意識形態的幽靈性特征進行了比較準確的描述:從宏觀上分析意識形態時,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對于那些幽靈似的東西的處理方式,實際上宣布或確認了馬克思常常賦予給宗教或意識形態的宗教性、神秘性或神學性的絕對特權。如果說幽靈賦予意識形態以形態或者外形的話,那么這也可以說就是宗教一類東西的本質特點。用馬克思的話說,這種特質就好比是剝去幽靈的語義學或詞匯外衣后,剩下的只是人們所無法抓住的價值。 這種價值與幽靈特質或多或少等同(夢幻般的、幻覺般的、魔幻般的、幻想的等等)。 ……這種留在宗教經驗之中的印記,即這種精神迷戀的神秘特點,首先是一種幽靈式的特點。⑤
幾句話中,德里達就用了“幽靈似的” ( phantomatic)、“幽靈” ( spectre)、“夢幻般的” ( fantasmagorical)、“幻覺般的”(hallucinatory)、“魔幻般的”(fantastic)、“幻想的” ( imaginary)、“印記” (mark)、“精神迷戀”(fetish)等幽靈批評中的關鍵術語來描述幽靈性:雖然關于幽靈的特點及其侵擾性只是德里達對馬克思主義的論述中的意外產物,但德里達對幽靈的定義貢獻卓著,并賦予幽靈以解構主義底色。其次,幽靈批評理論認為,幽靈實際上是人類意識和潛意識的投射。 文學作品中出現的幽靈、幻影、幻覺等實際上均源于人類的意識和潛意識。 從個人層面而言,幽靈往往源自人類無意識中一種被壓抑的恐懼,即弗洛伊德所謂的暗恐。 根據弗洛伊德的定義,“暗恐是一種驚恐的情緒,但又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就已經認識并熟悉的事情”①。
而暗恐的存在形式往往是復現。 但復現的形式并不是恐懼的原初形式,而是恐懼主體所不熟悉的或曰“非家的” ( unheimlish)形式。 但這種“非家的”東西又在某種意義上是經歷者非常習慣或熟悉的東西。 幽靈批評者認為,暗恐是人物壓抑在潛意識中的恐懼、焦慮等極端負面情緒,它常常以一種復雜的、不穩定的幽靈或幻影或幻覺的形式外化出來;在藝術表達層面幽靈元素又常常表現為時間序列、人物關系、敘事、語言等的不穩定性。
幽靈批評中的幽靈,還包括典故(互文)的幽靈性影響、作者的隱性存在等,這些都可以借助弗洛伊德的潛意識理論予以解釋。幽靈批評理論還認為,從集體層面而言,幽靈源于人類的集體無意識。 以尼克勒斯·阿布勒罕穆(Nicolas Abraham)和瑪麗亞·托羅克在其《狼人的魔語》及其系列論文中的觀點為例,可以看出幽靈批評者不僅運用弗洛伊德的暗恐理論來揭示人的心理投射機制,也運用榮格的集體無意識理論來解釋和分析集體的心理活動②。 榮格的集體無意識是一種心理的“空洞”(crypt),它暗藏了一切令人們痛苦、尷尬、羞于出口的過往秘密③。
這個空洞似乎具有魅惑力,激活人們心中各種記憶的幽靈,并將這些幽靈吸引到這些空洞中。 集體無意識理論為讀者與死者進行對話提供了可能。 另外,幽靈批評者通過運用集體無意識理論,也探討文學作品的雙重敘事的心理機制以及與語言的關系。 他們認為,在文本之下總有另一個文本,這個“另一個文本”即存在于我們集體記憶中的文學記憶,即前文本或典故,而且這“另一個文本”還有其前文本,如此無窮無盡,可以一直追溯到那個存在于我們集體無意識中的、處于人類“無知狀態”(unknowing)的文本。 這個潛藏在集體無意識的文本連同它之后的無數前/ 潛文本總是侵擾顯文本中的所有語匯。 在我們閱讀時,文本中的語匯、形象、情節、母題等都有前身,它們的初始形態可以追溯至其自身無法被理解的狀態,這種無法被理解和準確定位表達的狀態與無意識狀態很類似。
當然,若從幽靈批評的細部觀點考慮的話,幽靈批評理論還研究文學作者試圖超越文學前輩、擺脫他們如幽靈般侵擾文本的影響的焦慮。 前文本之所以出現或隱性存在于現文本,是由于作者對前文本既崇拜又希望超越而造成的復雜情緒投射的結果。 作者在文本中的隱形存在,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作者在潛意識中對自我定義的身份———作者是文本的上帝———的不自信心理或者作者與文本人物的心理認同的外化。 這種觀點可以說是哈羅德·布魯姆影響的焦慮理論的翻版。 此外,幽靈批評者認為,文學作品中的各種創傷,包括個人心理創傷和群體創傷、歷史創傷等,在文學作品中大多都外化成鬼魂、幻覺等心理病癥。 這也與創傷研究理論有諸多應和。 影響的焦慮也好,創傷也罷,均屬于心理學范疇。
再次,幽靈批評的核心觀點是“孤兒法則”。 文本被無數前文本以及無法被理解和準確定位表達的前身所侵擾,就注定了文學是無法被精確解讀的,批評本身就是一種誤譯和誤讀。 這一點與幽靈批評者的另一個觀點,即“孤兒法則”聯系緊密。 所謂“孤兒法則”,指的是某種體裁或母題或形象沒有一個固定的起源。 以文學體裁為例,任何一種體裁都能找到可視作是其前身的另一種體裁,但找到的這個作為前身的體裁又有其前身,如此往復,無窮無盡。 也就是說,任何一種體裁都永遠沒有真正的固定的前身,都是無父無母的孤兒,所謂的前身只是個幽靈式的存在。
正如“孤兒法則”的提出者龐特所言:[幽靈批評]遵循孤兒法則,強調沒有任何試圖找到文本的“父母”的嘗試能成功實施,也無法找尋任何文本的父系或者母系……。 它的模式是哥特式的,是蛻變的過去的顯性回歸———很肯定的是,我們對這樣一種過去的歷史確切性所知甚少,但這種過去卻不斷地影響我們對過去的應對方式,而且會妖魔式地發展,最終吞沒所謂確切性的可能性。
[…]它的典型形態不是語言,而是神秘費解的信息。 這種信息看起來總是處于不可理解的東西的影子遮蔽之下,經常自身包含著一種神秘費解的可能,這就好比我們總是讀到一張帶有字跡的紙的反面,或那張紙前面或后面一頁。 所以,文本對于解讀而言,總是一種“替代性文本”,一種不是解讀者要解讀的那個文本,一種被幽靈般改動了的文本,它原來的物質存在狀態是無法被解讀的。①
在論證“孤兒法則”的同時,龐特也總結了幽靈批評的實質,指出幽靈不是迷信中的存在或宗教所謂的鬼魂或靈魂,而是文學作品中那些由歷史、現實、作者、文學傳統等各種因素對文本形成的深遠的、揮之不去的、如同幽靈一般的不確定性影響。 也就是說,幽靈的特點是其不確定性、間質性和流動性。幽靈批評的實質就是研究這些幽靈,找出幽靈侵擾的方式、原因、根源、價值等。
三、幽靈批評的研究范疇
從本質上說,幽靈批評是一種綜合性的、跨學科的、以解構主義和心理分析為基礎的文化批評,其批評涵蓋“閱讀過程、作品人物、作者的潛意識、文化學意義上的集體無意識、歷史創傷、語言衍變、敘事結構等方面”②。 以杰弗里·溫斯托克(Jeffrey Weinstock)的《失望之橋:〈尤利西斯〉中的文本侵擾》為例,可以發現幽靈批評許多重要的批評范疇。 在該篇論文中,幽靈批評研究的范圍不僅涵蓋《尤利西斯》中死去的人的魂魄,還包括語言、記憶、作者等,這些幽靈都與破碎、缺場、死亡、痕跡、不確定性等相關。
溫斯托克從對莎士比亞、斯蒂芬的母親、布魯姆的父親及兒子等幽靈人物以及雷聲的所指和能指的幽靈性的分析入手,推導出“幽靈指向被壓抑的創傷的投射和病癥”③,凸顯了幽靈與心理投射之間的關系。 溫斯托克還將幽靈元素與潛在的敘事進程,或者說,雙重或多重敘事,有機結合起來,指出“文本對話式地超越自己的邊界,指向許多其他文本,打破了其內部的線性進程,因為文本中詞匯的復現使讀者偏離正題,將注意力轉向另一個語境和這個文本的其他部分” ④。
溫斯托克還通過分析斯蒂芬的父親和侵擾《尤利西斯》的喬伊斯,研究了現實中活著的人物(特別是作者)的幽靈性,并得出結論:無論是人物的意識還是詞語的所指,都受到父親的名字的控制,即其前人的意識和先前的所指的影響,前人的意識和先前的所指的確切根源無法回溯,這點也符合孤兒法則;作者的功能在文本中也是一種幽靈,無論怎么隱形或張揚,他的在場也是一種不確定性存在。
從溫斯托克的研究可以看出,幽靈批評在研究敘事進程的同時也更加科學地揭示了閱讀過程。 閱讀過程是一種與無數前文本幽靈的對話,它注定了這種對話是無法追溯到源頭的“失敗”之旅,一種無法得出確定性結論的努力,但也是一種意義非凡的對話之旅。從目前幽靈批評的實踐看,幽靈批評還包括上述未列舉的許多方面,例如人物間的隱性/ 幽靈關系。
這種關系不是現實中未被人發覺的、實際存在的秘密關系,而是陌生人之間在現實層面不存在的但在寓言意義上存在的關系。 以申富英的《論〈尤利西斯〉中作為愛爾蘭形象寓言的女性》為例,該論文研究了“共在變體”概念在《尤利西斯》中對人物關系所起到的幽靈式制約作用。 “共在變體” ( consubstantiality)既是一個宗教概念,也是一個哲學概念,指事物間具有相同本質但在形式上相互變化的存在形式。在《尤利西斯》中,“共在變體”的概念被大量運用到人物的寓言功能上,使得小說人物形成幾個寓言意義上的組合,數個人物分別寓示某個事物或現象的不同側面,而且一個人物又可以同時屬于不同的寓言類比組合,可以相互幻化①。
“共在變體”概念如同一個幽靈,它不斷地侵擾在顯性層面(現實層面)上毫無關系的人物,使得他們之間存在一種寓言層面(或者隱性敘事層面)的“共在變體”關系。 除上述文章提到的“共在變體”概念外,喬伊斯筆下有魅控作用的概念還包括“靈魂轉世” (metampsychosis) “變形”(metamorphosis)“三位一體”(trinity)“復影”(dark double)等。
這些概念的魅控作用在《都柏林人》中初露倪端,在《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中實驗性地發揮作用,在《尤利西斯》中最為綜合,也最為靈活,在《芬尼根的守靈夜》中達到高潮。 這些概念既是侵擾《尤利西斯》中幾個人物組內部存在的隱性關系的幽靈,也是控制《芬尼根的守靈夜》中人物塑造、情節設置、語言變形和主題表達形式的幽靈。幽靈批評雖然從字面而言是對幽靈進行的批評,但該“幽靈”不是玄學意義上的幽靈,而是與現實關系緊密、具有很強的政治性和倫理關注的概念。
戴維斯就曾指出,“侵擾學與過去大家至少近二十年內都明顯感知到的解構的倫理轉向緊密相關,而且也是這種倫理轉向的一個新的方面”②。 幽靈批評的現實關注和政治性可以從克里斯蒂娜·李(Christina Lee)主編的《幽靈空間與侵擾:缺場的情感》中略見一斑③。 該書密切關注西方現實問題,特別是恐怖襲擊、經濟下滑、精神危機等,通過研究文學作品中關于恐怖襲擊的記憶、家園的失去、礦業城鎮的消失、機場的廢棄、劫后的荒原等的書寫,系統地研究了幽靈的物質化、身體的空間化、消失的和死亡的人或物的重新顯形方式,以及這些幽靈頻繁地侵擾人們的心理空間和現實空間的現實政治原因。 借助研究幽靈空間對人類經驗的影響,該書凸顯了幽靈研究的現實性和政治性。
幽靈批評的倫理關注大多與身份研究密切相關。 例如皮潤(Peeren)的著作《幽靈式暗喻:活著的鬼魂和隱身的侵擾形式》就具有基于現實的政治性。 該書將幽靈批評置于現實的維度,試驗性地使得現實問題與文學研究、哲學思辨與政治、倫理等相互闡發。 該書作者認為,“幽靈”“魂靈”等詞常用來指涉非法移民、流亡者、仆人等邊緣人,因為他們的存在處于在場和缺場之間;如果這種指涉“頻繁使用,形成慣例,隱喻可以起到定義作用,將某些個人或群體定義為高人一等;亦可通過構建或強化負面的刻板印象剝奪其他個人或群體。”④基于此種機制,人類的指涉習慣會強化或解構共同體。
總之,幽靈批評是一種基于批評實踐、在與其他批評流派的互動中發展起來的相對松散的、綜合性很強的、以解構為本質的文學批評“流派”。 它認為文本、語言、文化和歷史之間充滿了矛盾性、非線性和復雜性,文學中的幽靈就是這些關系在文學作品中的具體化,這種具體化的顯現方式也具有幽靈性。文學閱讀是一種與幽靈對話的過程,文學文本充滿了各種“幽靈”的侵擾。 飄蕩在文本中的“幽靈”包括作者隱秘的思想、歷史無形而又無處不在的影響、前世和當世文本的“魅影”、當世意識形態的“侵擾”、作者或文學人物潛意識中被壓抑的愿望和精神創傷遺留的“暗恐”等。
幽靈批評的對象往往是具有高度解構主義色彩的文學作品,或者具有開放性或雙重(多重)敘事的文學作品,或者主題是關于創傷、壓抑等(無)意識的文學作品。 可以說,幽靈批評是研究文學的意義生成機制、文本的互文策略、雙重或多重敘事、置換策略、身份的流動性、人物間的幽靈式關系、文學作品中的瘋癲、夢境、幻覺等“怪異”心理等的法寶。 同時它也具有與它的名稱不太匹配的現實性、政治性和倫理性。
作者:申富英1,李英華1,2
轉載請注明來自發表學術論文網:http://www.zpfmc.com/wslw/3007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