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美國自白派詩人安妮塞克斯頓有一首詩,題為《當男人進入女人》,呈現了男女歡愛時的兩幀鏡像。為表述那妙不可言的瞬間,詩人兩次以邏各斯顯現為替代,暗示床笫動作推進到高潮與收束。邏各斯,人向無名之域不斷命名試錯的明證。這一用喻的出發點與喬治斯坦納
美國自白派詩人安妮·塞克斯頓有一首詩,題為《當男人進入女人》,呈現了男女歡愛時的兩幀鏡像。為表述那妙不可言的瞬間,詩人兩次以“邏各斯顯現”為替代,暗示床笫動作推進到高潮與收束。“邏各斯”,人向無名之域不斷命名試錯的明證。這一用喻的出發點與喬治·斯坦納稱“愛是非理性的必要奇跡”同理,指出了我們情感事件中的神性之維,即人類語言四壁所難安置的部分。愛是人類智識的非理性敵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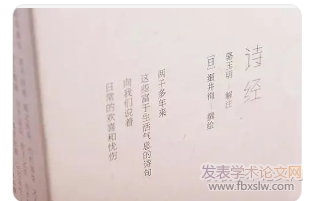
詩人安妮·卡森在其古典學研究首著《厄洛斯:苦甜》中開篇便嘆“薩福是第一個把愛欲叫作‘苦甜’的,戀愛過的人誰能駁回”。薩福天然地將情愛的癲狂迷魅歸咎于神諭的秘而不宣,開啟了一種苦痛襲來以求解脫的張力詩學—“當我看到你,哪怕只有/一剎那,我已經/不能言語/舌頭斷裂,血管里奔流著細小的火焰/黑暗蒙住了我的雙眼,/耳鼓狂敲/冷汗涔涔而下/我顫栗,臉色比春草慘綠/我雖生猶死,至少在我看來—/死亡正在步步緊逼”。
心意動蕩,隨即口齒無力自展,及至視覺熄滅、耳力失控、五體昏黑渾如被死亡攝取。這種在死生之軸上獲取刻度的情感強力(它絕不是修辭術,而是實有發生)直到中世紀仍然適用—但丁在地獄第五層聽了“被愛俘獲的故事”后,“仿佛要死似的昏過去”,“像死尸一般倒下了”。從古希臘作品中,卡森還識別出“愛人—(受阻的)愛欲—被愛者”的位移關系,提出欲望的受阻反而是世間情事永葆盎然的要義:欲望被延緩、受阻滯,這令愛人者朝向被愛者終究是無法抵達的趨近。
這一過程恰似以智性揣度神意,或以語言趨向太一。在“苦甜”織造的引力之網中,我們體嘗愛情節奏的驟變與焦點的挪移,用薩福的詩行來說:如果現在逃避,很快將追逐;如果現在拒絕,很快將施予;如果現在沒有愛,愛很快就會流溢。這是西方情詩給人的第一印象,其中矗立著一個完整的希臘。只不過這個希臘遠非我們所能在場。
就像伍爾夫盛贊“每個單詞都充滿生機,傾瀉出橄欖樹,神廟和年輕人的身體”,這些身體,我們是在石膏模型和博物館走廊的大理石座上結識的。事實是,薩福情詩里那種相顧失色的驚怪,那種“雖生猶死”的薩滿式的剖白,不可能從今人口中說出而不顯得失態造作。正如伊格爾頓認為伊麗莎白·勃朗寧的十四行詩“對現代趣味來說太嚴肅、高尚了”,包括趣味在內的各個范疇總在發生變革。勃朗寧情詩底下籠罩著的教堂燭光、英格蘭灰,以及由大寫的“正義”(Right)和“贊美”(Praise)為尾音的維多利亞時期的激情,現在讀來未免顯得邈遠、寡淡。這不是要把過去和當下對立起來。
事實是,一首詩縱使寫自異時異地,也能以種種方式找到你。好詩理應是對現時與個例的超越,這方面,從密爾(JohnStuartMill)到波德萊爾到T.S.艾略特都有相 承性的論述,盡管角度有所偏差。他們的當代信徒、美國詩評家斯蒂芬妮·伯特聲稱,“讀抒情詩就是為了發現跨越時空的人類情感的共性,無論多么雷同、多么主觀”,因為“詩歌是感情的語言模型”,既然二十世紀的T.S.艾略特能被十七世紀的約翰·多恩打動,原因之一便是前者詩中的某些感情至今仍在。
T.S.艾略特倒未見得從抒情詩的角度立論,但他對藝術何以喚起共情有一個著名的推演:用藝術形式表現情感的唯一途徑,是找到一個“客觀對應物”;換句話說,是用一系列實物、場景,一連串事件來表現某種特定的情感,要做到當那些最終必然是感官經驗的外部事實一旦出現,便能立刻喚起那種情感。這是“情同此心”的慢動作分解。按照艾略特,當我們產生共鳴時,彼此內心狀態的等值物是以“外部事實”—“一系列實物、場景,一連串事件”—為中介來兌現的。這里的“外部事實”同寫作時代或作家傳記無涉,而是指內置于文本的敘事情境,也即后來新批評派在講授一首詩時,要求投以細讀的入門要素。在新批評派看來,一首詩的情感接應是否順遂,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這情感所形諸的“外部事實”塑造得是否明晰、合宜。
后來,“艾略特-新批評”聯盟遭到眾所周知的抗辯。原因是人們意識到,詩歌的書面流傳和視覺接受終會令詩人在“外部事實”中注入的語調變得暗啞,從而讓寓居其間的情感揚抑遭到誤讀—這與新批評派自己提出需加以謹防的“情感謬誤”與“意圖謬誤”并不相去甚遠。如果跨時空共情的保值性不過是一個夢想,那么,我們在當代詩歌中收獲的熨帖感是否就相對安全無虞?不論如何,有一點或許可以確定,“現代世界有它的依傍之物”(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語),在同時代詩人所提供的、比例更為適中的“外部事實”里,我們的關切與歡娛更易被可視可觸可體味的事物所牽引。這方面,情詩尤是如此,因為情詩與我們的身體感覺最為關聯。
當艾德麗安·里奇說“我與你同在……”而“莫扎特的g小調從錄音機流出”時,無須轉譯,質地相同的樂聲會親手撫梳我們的心靈,帶我們重返那個未曾移位的夜晚。同樣地,當在麗澤·穆勒的詩中讀到“你那悠長的,流暢動聽的詞語/像熟透了的牛油果”時,這樣一個喻體會從我們的口腔吸入,溶解在雙顎的后排。事實是,對一首情詩的理解必然在所有感官的聯覺旋渦中完成,城市的落日可以目睹而汽車的嘯動得以耳聞。如果閱讀情詩時因過多的陌異感而停頓下來,那么,這種停頓是致命的。
詞語在經驗現實中尋獵,隨時咬合其捕獲物,這在情詩中尤為矚目。美國當代詩人從惠特曼身上,保留了大規模列舉事物的興味、對自由律的偏愛以及使用情色語匯時的坦率。其中,《雅歌》那種對身體部位的掃描式稱頌,由自白派與“垮掉一代”經手,已然成了一枚獨屬于“美式”的簽章:……厚實緊湊的胸肌,乳頭像嶄新的硬幣印在胸脯上,下面的肌肉扇子一樣展開。我察看他的雙臂,就像是用了一把刀沿著條條曲線鏤刻而成的造型,三角肌,二頭肌,三頭肌,我幾乎不敢相信他是人類—背闊肌,髖屈肌,臀肌,腓腸肌—如此完美的造物。
—金·阿多尼茲奧《三十一歲的戀人》似乎什么也無須克服,美國情詩的領地,天然就為身體感覺而劃劈。肉體的私語與細響,在直露的日常生活體驗中再度開口。基于廣義的現實主義,詩人們無意于凈化或參透,而是欲將情思的瑣屑與生理分泌物的熱味無損地還原。和惠特曼的異域繼承者聶魯達(布魯姆語)一樣,美國詩人寫起愛情,用的也是舌、指尖、眼耳與鼻息。羅蘭·巴特在談及《戀人絮語》的寫作本意時稱,“戀人的表述并不是辯證發展的;它就像日歷一般輪轉不停,好似一部有關情感的專業全書”。
與此相仿,任何一種美國當代情詩選編,都有其重要的辭典學意義。這些獨具美國特色的“工作坊詩歌”(workshoppoetry)整體上呈現為一種與中產階級審美合謀的“內室敘事”(比利·科林斯寫道:“我看不到千里之外的你,/但能聽到/你在臥室里咳嗽/也聽到你/把酒杯輕輕放在臺桌上”),為種種情態所擺布的戀人們,仿佛總是落座在家中(書桌前、起居室、廚房或床上)、在可調節的室內光線下,將情感經驗被詞語轉述出來的快慰分享給(同樣在室內的)我們。這些內室敘事不僅搬演我們愛情的諸般歡樂、不幸、饑渴、潰敗與狂喜,同時也是對當代城市生活語匯的集中編目。
比如,C.D.萊特以第一人稱寫道:“我會把雙腿像一本書那樣打開……我將像一本酒水單、一只青口貝那樣打開”,當身體與消費品之間的界檻消失、相互喚來時,諸如“酒水單”和“青口貝”就遷入了新的意義居所;再如,在里奇那里我們讀到,相愛的偶然性“就像車輛相撞,/就像書會改變我們,就像我們逐漸喜歡上/新近住進去的某些街區”,大城市的生活界面被唾手組合成情感表述的語義場。又如斯蒂芬·鄧恩(StephenDunn)的溫存回憶:“而我/當時所知道的/只是汽車的后座和睡袋/暗夜里偷偷摸摸的一晚兩晚。我們在/同一個辦公室工作,打趣和孤單/把我們引向一個共同的秘密”。暗色調的私人生活展示,重新編輯了語言對現實的抒情,將隱沒在背光處的城市愛情常景調制成可能的感悟和灼見。
很顯然,美國當代情詩有其切入當下的銳度與速率。在以知覺力為驅動的閱讀過程中,感官自動完成了那種調適。每首詩都像是為你而寫,未經引介就曾熟識、在布局無異的城市街區頂部將我們隔空捕獲。如同美國文化制版的一份拓印,這些情詩復寫著時代的肌理,它們展現了美國式的對各色人種與性取向的兼容并蓄、對情感的實用主義體悟,以及對日常物象的美化沖動。在講述現代交通、品牌消費、技術更新和賽博媒介等對我們情感生活的重新定義:一只橘子,去皮,分成四瓣,盛開著就像威治伍德(Wedgwood)瓷盤上的一朵水仙什么都可能發生。
—麗塔·達弗《調情》“什么都可能發生”:一個正在敘述的戀人,成為我們內心語流的外化。他或她分享的信條是,所有的體驗都是有價值的,無論巨細:陡然而發的性欲、讓身體發疼的回想、顯而易見長期容忍的謊言、劇情展演般的調情、異地戀難以飽饜的思慕、通信失聯的懊惱、愛上一個不該愛的人……仿佛同是一個“我”在產生、發展、流動、敞開;沒有一個情境不值得描畫,沒有一個物件不該被展開度量。
這種細細逡巡的背后,飽含著對于每一個時間單位及其容納的生命經驗行將萎縮乃至熄滅的焦慮與忌憚。畢竟,生活結構于偶然與碎片,愛也即生即死,這或許是原子化時代下唯一恒常不變的真實。所以昂立·科爾在《眼睛泛紅的自畫像》中寫道:“我曾喜歡每天/都會在我們身上發生的小小的生和死。/甚至連你明亮的牙齒上的白色口水/都曾是愛的泡沫。”
梅洛·龐蒂曾在一篇文章中談論塞尚:“對于這位畫家而言,情緒只可能是一種,那就是陌生感,抒情也只可能是一種,那就是對存在不斷重生的抒情。”在他看來,塞尚通過描繪日常物件來翻新聯覺體驗,這恰似現象學“回到事物本身”的自我期許。畫家不斷拿起世界,如“陌生化”對材料的藝術安排那樣,反復為靜物和風景注入新的色彩、比例和陰影。這種塞尚式“陌生感”,即感知定式的變異,能引發知覺上的驚訝與震顫,是將邏各斯放逐遠征的眩暈沖動。當珀涅羅珀牽起奧德修斯的手,并不是不讓他走,而是要把這份安寧壓印在他的記憶里:從今往后,你穿行而過的所有靜默都是我的聲音追趕著你。
文學論文范例: 網絡時代漢語言文學閱讀體驗探究
這是一番刻骨的情話。一個生命楔入另一個。也像詩行,找到了一只同情的耳朵—這是美國當代情詩所向往的實際處境:這些詩歌每每由一個可信任的言說主體引領著,通過現在時的講述從我們身上貫穿、駐留、直到變為我們身上可攜帶的一部分。與前述詩人用語詞捕獲經驗的努力互成鏡像的是:到了閱讀環節,讀者將從詩中習得必要的語詞,以備為自己的經驗命名。或者是,閱讀時因惺惺相惜而珍藏的句法,能夠在未來某個經驗降臨時脫口而出。這或許是詩歌共情術所能引獲的最好報償。說到底,沒有什么理由使我們必須相信這些情話,然而我們還是相信了。
作者:張逸旻
轉載請注明來自發表學術論文網:http://www.zpfmc.com/jylw/28119.html